陕北的秋天是从山梁上第一株高粱低头开始的。那抹红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从夏日的青绿里慢慢沁染出来的,先是一点羞涩的绛色,继而以燎原之势,漫过了千沟万壑。黄土高原那亘古的苍黄底色,忽然被饱满的红、沉甸甸的金、玉米林顽强的绿切割点染,铺展成一幅深沉的丰收画卷。
风是最高明的指挥家。它掠过连绵的谷子地,万千穗子便齐刷刷低下头,沙沙作响,如无数金铃摇荡;闯进苞谷林,宽长叶片相互摩挲,飒飒有声,似海潮涌过深谷;最后盘桓在场院上,扬起轻尘,将农人酣畅的笑语传向远方的山梁。这声响里没有半分文人悲秋的萧瑟,唯有土地馈赠的丰厚与生命奔流的踏实。
农人们与土地肌肤相亲,懂得每块田的脾性。收获时节,男人手持镰刀,弓着与土地平行的脊背,在金色浪潮里前行。锋刃过处,谷秆应声而断,被熟练地揽入怀中,成捆扎实。汗水沿古铜色脸颊滑落,砸进黄土瞬间消失,仿佛被焦渴的大地收回,预备着来年的承诺。女人和老人紧随其后捆扎搬运,各色头巾在田地里星星点点移动,像是大地上开出的最坚韧的花朵。
场院上,新收的谷粟被高高扬起,借助风力分离秕谷与籽粒。金灿灿的粮食如雨瀑落下,堆成小小金山。孩童在丰收的“战场”嬉闹穿梭,偶尔被笑骂着驱赶,又偷偷抓起带日头温度的麦粒塞入口中,咀嚼出满嘴新粮甘甜。那甜味,是秋天最真切的味道。
日头西沉时,天边的云烧得如同炉中烙铁。炊烟从各家烟囱袅袅升起,是归家的信号,是温饱的许诺。饭桌上定然有一碗新熬的小米粥,金黄粘稠,氤氲着土地最醇厚的香气。农人们围坐默默吃着,一整日劳作的疲乏,被这大地最直接的馈赠所熨帖。
在这深秋的黄土地上,美得毫不矫饰。它的美是汗珠摔入泥土砸出的八瓣晶莹,是镰刀划过秸秆奏出的铿锵节拍,是粮堆持续生长的沉静力量,更是农人被夕阳拉长、与千沟万壑融为一体的身影。这景象,是一部用劳动写就的磅礴诗篇,吟唱着生息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自然之间最深沉的契约。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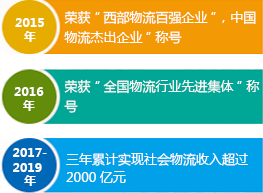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