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撕开六月的夜幕时,我总会想起陕北窑洞的夏天。那些黄土堆砌的冬暖夏凉的居所,藏着我生命中最鲜活的盛夏记忆,即便隔着千里山河,仍能听见夯土墙里传来的旧时光回响。
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爬上窑顶,照得土墙上斑驳的麦秸茬闪闪发亮。奶奶佝偻着背,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支起案板。露水未干的案板上,新割的韭菜泛着翡翠般的光泽,菜刀起落间,混着葱花的香气在晨风里打着旋儿。“碎娃,去窖里取块老豆腐!” 奶奶的喊声惊飞了枣树上的麻雀,我猫着腰钻进阴凉的地窖,指尖触到陶瓮里沁着凉意的井水,捞出裹着纱布的豆腐块,水珠顺着指缝滴落,在黄土上砸出小小的坑洼。
窑洞前的打谷场是夏日最热闹的地方。正午的太阳把场院晒得发烫,男人们光着膀子挥舞木锨,金黄的麦粒在头顶划出抛物线,落下时扬起细碎的金粉。女人们则在窑洞阴凉处纳鞋底,银针在蓝印花布上穿梭,偶尔抬头看一眼疯跑的孩子。我和小伙伴们顶着烈日在打谷场边的沙棘丛里钻来钻去,被刺扎得龇牙咧嘴,却还是执着地寻找最红的果子。直到喉咙被暑气燎得生疼,才想起跑回窑洞,掀开粗布门帘的瞬间,裹挟着艾草清香的阴凉扑面而来,恍若跌进另一个世界。
窑洞的夏夜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夕阳把天际染成酡红,燥热却仍未消散。老人们搬出榆木小桌,在窑前空地上摆开阵势。爷爷用旱烟袋敲着青石凳,慢悠悠地讲古朝的故事,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在暮色里画出神秘的轨迹。我们这些孩子趴在石桌上,看奶奶用井水湃过的西瓜裂开清脆的声响,红瓤黑籽的甜蜜顺着嘴角流淌,混着夜风里飘来的荞麦花香。银河在头顶渐渐清晰,萤火虫提着绿灯笼在枣林间游荡,不知谁家的收音机里传来信天游的调子,苍凉的嗓音裹着岁月的沧桑,在窑洞群间悠悠回荡。
最难忘的是雷阵雨突袭的夏夜。墨色的云团压得很低,风卷着沙尘拍打着窗棂。奶奶忙着用麻纸糊住窗缝,爷爷则把晾晒的谷草往窑洞里收。雷声轰隆滚过天际,闪电照亮了远处连绵的峁梁,紧接着豆大的雨点砸下来,在窑顶上敲出密集的鼓点。雨水顺着排水沟汇成小溪,带着黄土特有的腥气漫过脚面。我们趴在窗台上,看雨帘中窑洞的轮廓变得模糊,听着雨声、风声、雷声交织成的交响乐,心里却格外安宁 , 只要躲在这厚实的窑洞里,再大的风雨都不足为惧。
后来离开了家乡,每到夏天,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窑洞。闻到韭菜盒子的香气,眼前便浮现出奶奶在案板前忙碌的身影;听见蝉鸣,耳畔就响起打谷场上木锨扬起麦粒的簌簌声;看到夏夜的星空,记忆里的萤火虫又开始在枣林间飞舞。城市的夏天被空调割裂成支离破碎的片段,再没有那种与自然浑然一体的酣畅,也寻不到窑洞前那份淳朴的烟火气。
如今,老家的窑洞大多已无人居住,斑驳的土墙在岁月中渐渐坍圮。但每当夏天来临,我依然能在梦里回到那片黄土地,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重新拥抱窑洞里的阴凉与温暖。或许乡愁就是这样,它早已深深扎根在记忆深处,化作夯土墙里的麦秸,化作窗棂上的剪纸,化作永不褪色的夏日画卷,无论走得多远,都能在某个蝉鸣聒噪的午后,将游子的心轻轻牵回故乡。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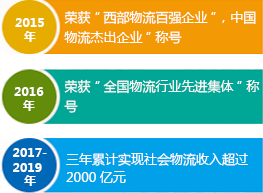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