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来时,东风正软。泥土解冻的气息混着草木萌动的清香,在晨光里浮动。远山还笼着薄雾,近处的田垄已泛起新绿,像打翻的颜料在宣纸上晕染开来。这个时节最是奇妙——死亡与新生在此刻达成某种默契,坟头新培的黄土旁,野花正开得恣意;扫墓人沉重的脚步下,蚂蚁已开始搬运春粮。
每当纸灰如白蝴蝶般纷飞,我总想起祖父生前的模样。他惯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将锡箔折成元宝的形状,每一个褶皱都透着郑重。如今轮到我跪在青石板上,看火舌舔舐纸钱,忽然明白,祭祀从来不是给逝者的供奉,而是生者自我救赎的仪式。香烟袅袅中,记忆中祖父的面容,时而清晰如昨,时而又模糊难辨,最终化作碑前一缕轻柔的微风。祖父虽已离去,但他正直勤劳的品格、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早已如同一颗种子,在我心间生根发芽。
孩童们清脆的笑声,突然打破空气中的凝重。他们手持彩线,在广阔的原野上尽情奔跑,纸扎的鹰隼、沙燕等风筝,恰似灵动的飞鸟,扶摇直上,将生的喜悦书写在澄澈的云端。
清明雨总下得恰如其分,细密的雨脚走过青瓦,在檐角串成水晶帘幕。撑着伞走过长街,看见糕点铺蒸腾的热气里,新制的青团碧如翡翠。老板娘说:“艾草是昨儿才摘的,最嫩的时候。”这让我想起《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的“子推燕”——用面捏成飞燕,用柳条串起插在门楣。千年的风俗流转至今,人们始终用最鲜活的春之馈赠,对抗死亡的腐朽,传统的力量不仅留存于食物与习俗之中,更在现代社会绽放出新的活力。
案头山桃花影斑驳,翻检旧照,我惊觉逝者留下的远不止回忆。祖父栽的紫藤今已亭亭如盖,教的童谣还在小辈口中传唱,窗外流萤闪烁,恰似那些未曾说完的话语,在夜色中若隐若现。我深知,祖父给予我的力量,会伴随我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
破晓时分,扫墓人留下的脚印里,盛满了露水,宛如大地的泪痕。但当朝阳升起,所有的潮湿都将蒸腾化作云朵。我采撷野径边的蒲公英,看着绒球在掌心轻轻飘散 —— 这或许是清明最深刻的隐喻,告别与新生本就是一体两面。祖先长眠的土地上,麦苗正在茁壮成长;我们带走的行囊里,装着古老的智慧与不灭的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份希望将支撑着我们在事业上拼搏奋进,守护家庭的温暖,为社会贡献力量。
清明,是中国人最具诗意的生死课堂,它教会我们在缅怀中汲取力量,在消逝中见证永恒。当纸灰化作滋养生命的春泥,当哀思转化为蓬勃的生机,我们终于明白,最好的怀念,是带着逝者赋予的光芒,把未走完的路途,走出万丈光芒。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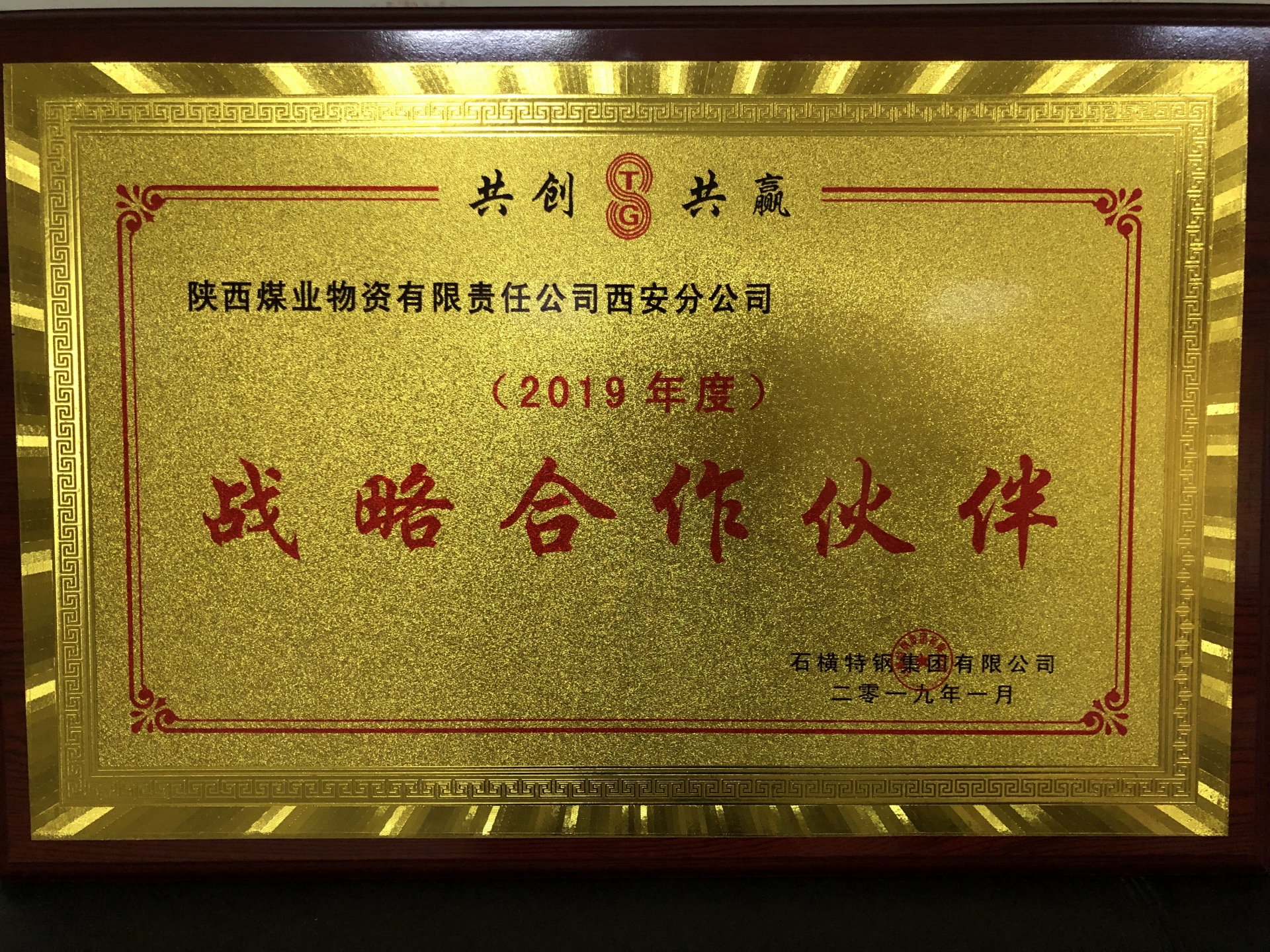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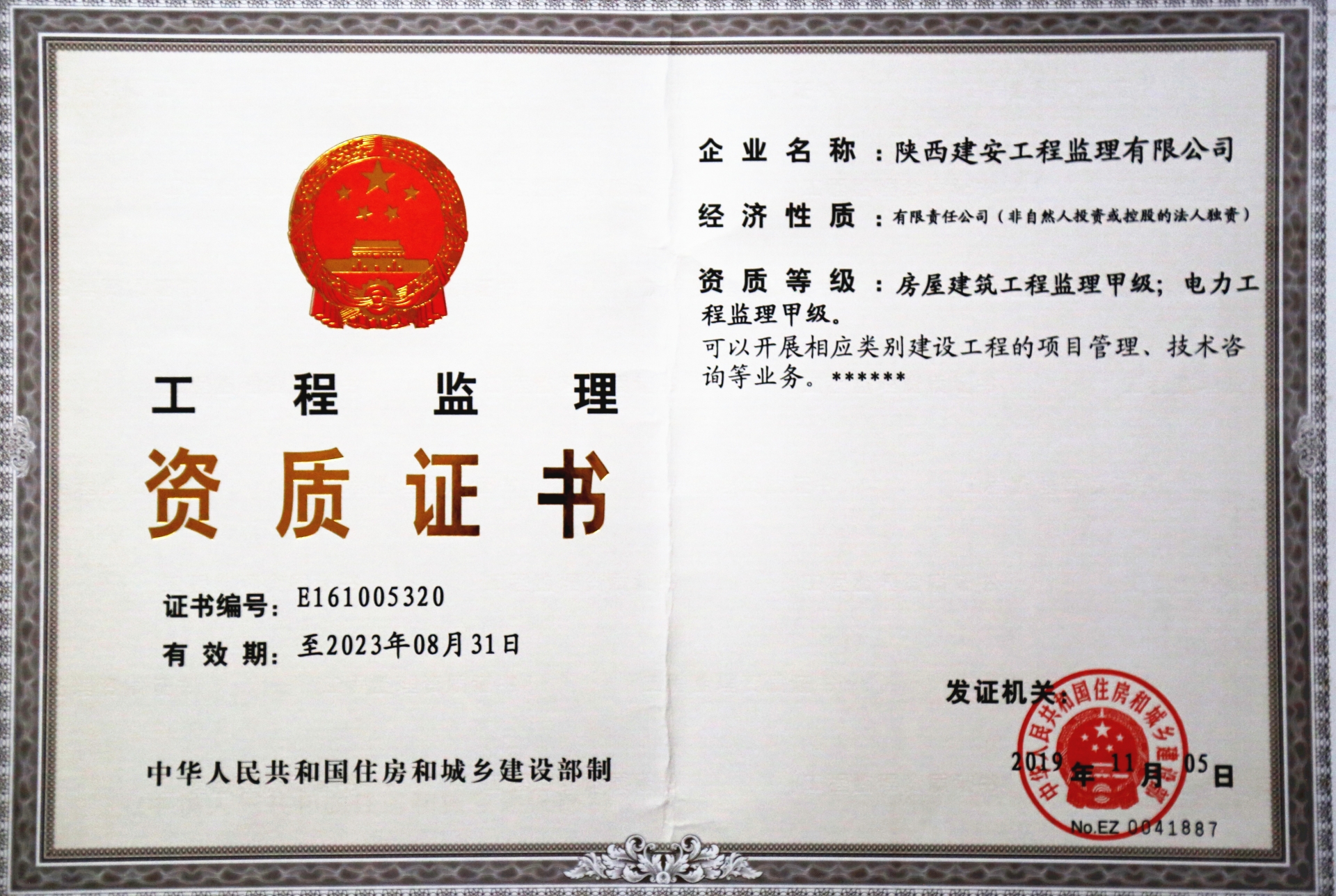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