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过后十五天,清明如期而至。清明是个内涵丰富的节日,祭奠逝者,缅怀追思,数千年来孕育出的人文与精神值得珍惜。
年少时不识清明,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简单的方块字,和其他词汇没有什么不同。稍大些时,清明节跟着父母给祖先上坟,我才知道了清明节是上坟祭祖的日子,据说这一天,无论干什么都不犯忌。天上太阳很大很亮,却照不到黄土之下的眠床。它只顾慷慨地照耀着坟地里那些花花草草,并把黑森森的影子投射进我的心里。
看着父母严肃的表情,一锹一锹给坟上培土,摆祭品,焚纸钱,烟火明灭中透出难言的诡异,我只想逃离。
高一那年,我的同学遭电击身亡,听旁观者讲:灯泡的屁股硬生生的击穿了他的一个手指,他的16岁青春就这样被黄土收留,既没保留遗体也没有坟茔。生命如此不堪,黄土从不挑剔,无论是八岁还是八十岁,只要它喜欢,它可以一概揽在怀里。
那一年的清明节,我很想去为他扫墓,渴望为自己的思念寻一处安放之所,然而终是没能成行,那时的我心中对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感觉很近,不想面对更不敢面对。
我在一年年地成长,另一些长辈日渐老去逝去,爷爷,奶奶,舅妈,姑姑,恩师,同学,战友……他们一个个远去,不留痕迹,没有归期。
清明节,我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扫墓,祈祷,对于死亡的恐惧也年复一年的扫墓中淡了。
每年的清明节,行走在车轮滚滚的扫墓人群中,看着坟上的新土,墓碑上的淡菊,燃一只香烟,洒几杯薄酒,烟雾缭绕着思念在碧野晴空里升腾,我的内心有一种无言的感动。
我敬重这种朴素的人伦温暖。长眠于地下的人,活着时曾经一次次扫着亲人的墓,而今亲人在扫着他们的墓,如此代代相传,源远流长,心存感恩之心。百年之后,或静卧成丘,或耸立成山,一块碑,一粒尘,在岁月的轮回里,依然彼此守望,留存的是一代传一代的思念。黄泉与人间,每个人的来路和归途是脉络清晰,爱在时空间辗转,传递。生死看淡,人性看重,无论有多大的纠结都放下,处处才能散发出朴实的大爱之光。
清明到了,回家扫墓祭祖吧,然而又能回哪里去呢?这是无数漂泊者的心伤。一辈又一辈,人就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祖籍简化成心坎中一个生了根的名字。后来,地球成了一个大村子,飘洋过海不再是什么难事,脚步自然越行越远。回望故园,故园却在目光所不能及的远处,陌生的想不出模样。只好在心中想象:故乡的柳树又绿了吧,先人的坟上应该芳草萋萋。
三杯浊酒下肚,乡愁开始在血管里叫嚣,游走。此时,如果窗外飘着清明雨,疏疏斜斜,清清冷冷,点点敲打着心头,竟会连那眼眶里也汪起思乡的水来。山水迢迢,乡愁是被打湿了翅膀的鸟,飞不过关山万千重。
每年的清明这天,我喜欢找个僻静的地方,面向关山的方向,一年一度和逝去的长辈对话静静展开。爷爷,奶奶,父亲,二叔,大姑,大舅妈,姨妈,他们有的陪我长大,有的到老都没见上一面,我说着,他们却沉默不言。然而我并不觉得害怕,我相信他们就在我的身边,看着听着。父亲和几位亲人的坟在粮食地里,这个时节,坟上新草渐生,野花点点,周围桃花开着落着,蜜蜂戏着舞着,绿杨晴川里,阡阡连陌陌,守护着他们的家园。
这个时节的天空是很干净的蓝,阳光明媚而柔软。清明风里,踏青的人放起造型各异的风筝。风筝的翅膀上方有大片的云朵聚了又散,这种时而白云时而苍狗的游戏悠然。
清明折柳是古人的一种风俗,有些地方流传至今。柳枝,被赋予了避邪保平安的重任,这种原本普通的植物变得不一般起来。其实也未必一定是柳,野花鲜草未尝不可。踏青归来,把顺手采撷的花儿或者柳枝插于门上,身上还留着郊外清风芳草的味道,好像把整个春天一起带回家了。
古人实在可爱,喜欢直白而浪漫的情怀,每每读之,心头如沐暖阳,恨不能自己的发间也立时生出一朵野花来。相比之下,现在的人与自然界和谐相依反而要稍逊一筹。
清明就是这样,生者与死者相互守望,哀与乐陪伴同行,让我感悟到一种超越生死的豁然与达观。燃香点蜡,焚烧贡品,一定要注意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苍凉的声音总能无来由的穿透我的灵魂,体味一种烟火人间的人情味和安全感。
天地清明,一切平安是多么深刻的词汇,顿感轻风拂面,天地宏明,人畜安然。
清明已近,春耕将始,惟愿风调雨顺,天地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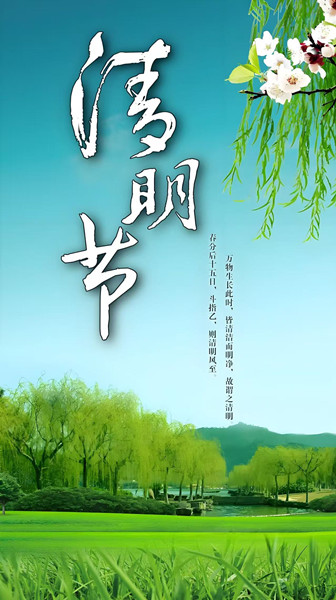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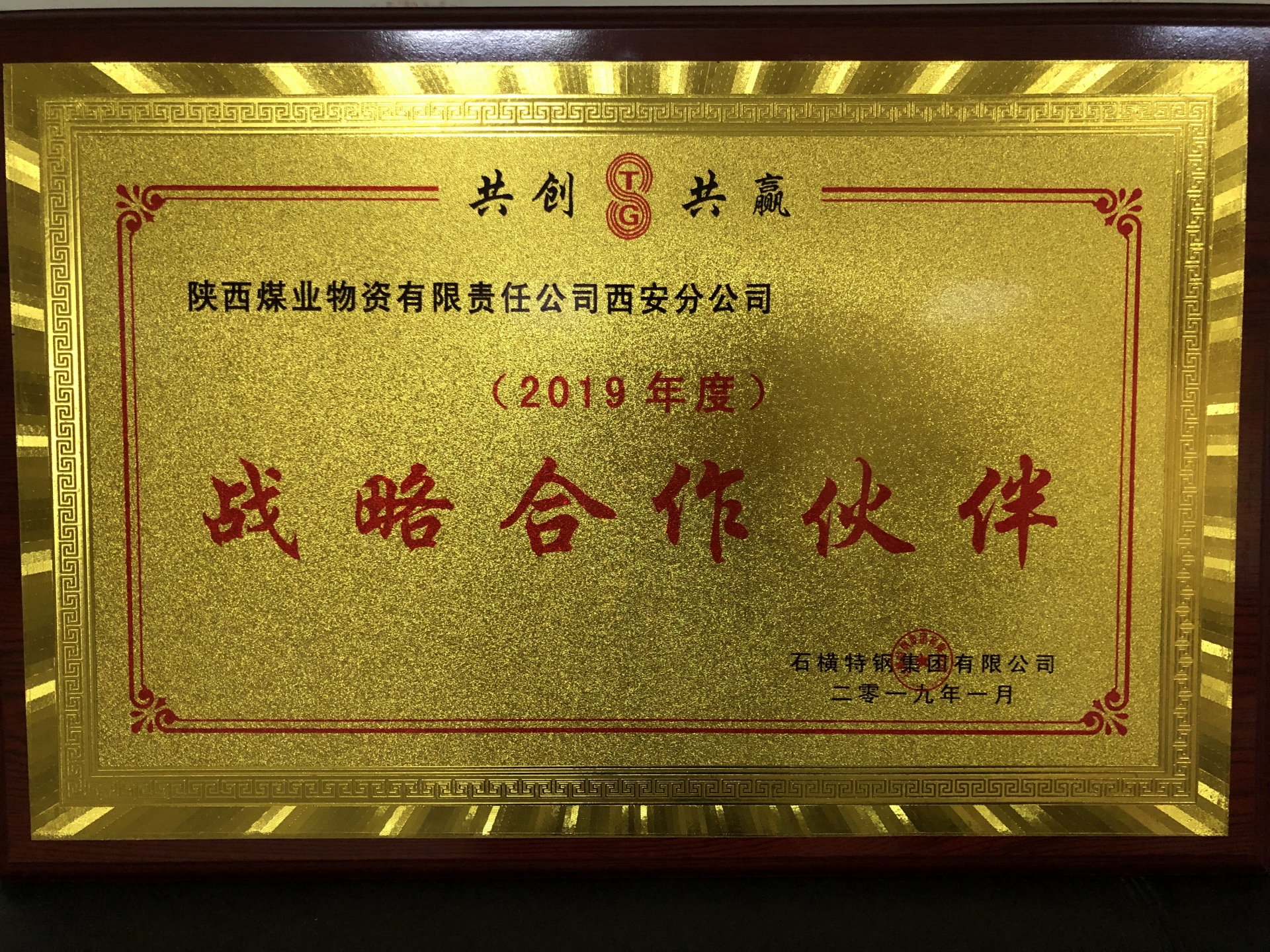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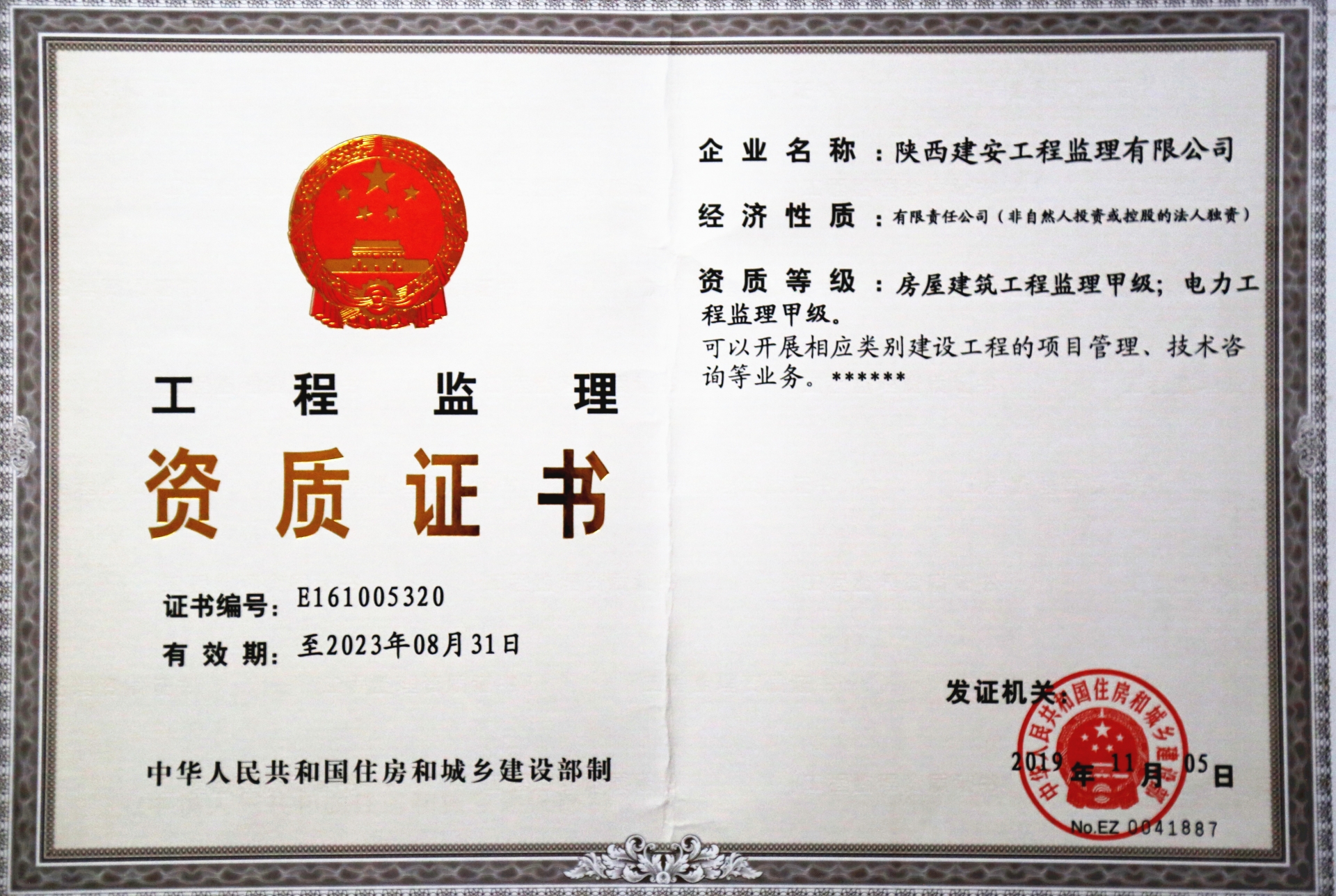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