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屋重新修葺的喧嚣里,一方粗陋的泥巢赫然闯入我的视线。粗砺的泥垒,几缕枯草粘附,杂乱地贴在混凝土墙面上,巢内几只雏燕嫩黄的喙如花苞初绽般开合,成燕如一道深情的闪电,将衔来的食物探入雏燕口中,旋即又振翅消失于天际——那疾飞的身影,是生命最动人、最不知疲倦的奔赴。
这小小泥巢,瞬间如钥匙开启窖藏已久的童年,窑洞里的灯壳旁,也栖着这样一方燕巢,春燕是窑洞里的贵客,总搅动满室生机,让冬寒的冷清退却。父亲常立于炕沿,目光温存,轻语叮嘱:“别惊扰它们,燕子是客”。幼时的我,趴在炕沿上看成燕衔虫归巢,喂入雏燕嫩黄的口中,竟以为那是人间最精彩的戏剧。父亲的话语,如春风中飘落的柳絮,无声却郑重地栖落在我心田,教我守护这小小的巢穴。
如今,儿子仰起小脸,指着燕巢问我:“爸爸,燕子会一直住这里吗?”我轻抚他的头发,将父亲的话换了词句:“燕子筑巢是吉祥和好运的象征,要守着这巢,别惊扰它们。”成燕掠过的弧线,与记忆中窑洞上空的轨迹悄然重合。儿子的追问,恍如当年我缠着父亲问燕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原来有些传承,就藏在燕翅的轮回里,父亲的叮咛,借燕子的翅膀,越过时间,栖落在我的唇间,又飞向下一颗稚嫩的心。
阳光斜镀燕巢,成燕剪影而归,雏燕的呢喃仿佛岁月河床的私语。儿子拽着我的衣角,听我讲窑洞旧事与童年趣闻。这方燕巢,不仅是鸟儿的家,更成了一道桥,连起窑洞的昨日与今日门前的对话,父亲的话语如窑洞中流泻的阳光,落进儿子澄澈的心湖,在岁岁燕语中,酿得愈发醇厚清晰。檐下这方寸天地,何止是燕巢?它早已成为我灵魂的檐角,在尘世奔忙的风里,每当新泥混着草茎落上梁木,仿佛照见生命最本真的纹路:那纹路里刻着平凡砾石的坚韧,写着枯枝续春的执念。我也愿如这檐下的生灵,为心中那方暖巢,勇敢而坚定地飞翔,衔泥衔草,不避风雨,在无垠人世筑自己的巢,织一隅安稳春秋。只为那归巢一刻的温热与安稳。
也许,修缮老屋的意义,正在于此,不仅修葺风雨剥蚀的砖瓦,更是在时光的缝隙里,将父辈手中递来的那份守护与温情,用新的泥草,小心筑进檐下的燕巢里,也筑进孩子明净的眸光深处。生命如燕,代代衔泥补巢,守护的早已不止是砖瓦梁木,而是血脉里流淌的“家”的温度。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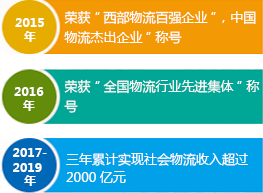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