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的春天是从风的褶皱里渗出来的。起初不过是晾在铁丝上的棉手套不再板结,某天清晨突然变得蓬松柔软。接着是配电箱外壳上的霜花,撤退时留下蜿蜒的水渍,像谁用指尖在铁皮上画了条隐秘的暗河。直到某个黄昏,站在库房门口,忽然有被晒暖的细沙钻进领口,却不是往日的坚硬。
人们总说陕西的春天短得像句被吞掉的叹息。可那些躲在混凝土裂缝中的生命,分明在编织更绵长的叙事。老围墙根部的苔藓开始泛出铜绿,被车轮反复碾压的野草从柏油路裂缝探出头。
工作服渐渐混进了不知来处的草籽清香,午后阳光斜射进库房,漂浮的尘埃突然有了琥珀的质地,让人错觉每粒飞旋的星子都裹着枚微缩的春天。
库房背后的积雪撤退后,露出被盐渍浸透的土壤。那些灰白的结晶竟开出花来,在某个无人注意的清晨,化作满地闪烁的碎钻。穿堂风里开始携带未知的甜味,像童年时藏在铁皮盒里的水果硬糖,剥开半透明的糖纸,才发现内里裹着蒲公英的绒毛。
在这个季节里,我常常会想起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春天就像一位智慧的长者,用温暖与生机告诉人们,寒冬再漫长也会过去,希望总会如期而至。
榆林的春天,没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秀丽,没有塞北草原的广袤豪迈,但独特的粗犷与柔情,让我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力量,领悟到生活的美好与珍贵。
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生长、绽放,像春日的花草一般,努力向着阳光;那些被冬天收缴的色彩,在空气中重新聚合:旧铁轨上的锈红变浅了,运煤车辙的灰黑变淡了,连安全帽的明黄都褪去几分冷硬。
不必追究楼前桃树何时结苞。当砂石路的裂纹里爬满草书,当所有坚硬的边界都泛起毛边,塞北的春天便完成了它精密的解码——我们不过恰巧站在金属与风沙的间隙,接收到了万物舒展的波长。
傍晚时分,新叶在暮色中摇晃,投下的影子像谁用黛青的墨在砂纸上写信。踩着渐渐松软的土路往回走,忽然明白春天从不需要确凿的物证——它只是让每个赶路的人,突然想在风中多站一会儿。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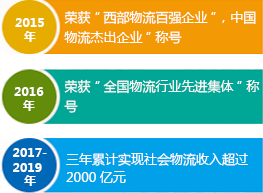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