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
儿时的记忆总是清晰又模糊,我可以想起玉米丰收时家家户户夜里点灯掰玉米粒儿的尘烟;可以想起雨天潮湿的青苔扒在家门口的石板台阶,麻将馆前的泥路积水难行,主人家放了一块块转头以供牌友进入,孩童们把树叶扔进水面又拿树枝挑起,叫着笑着说自己钓到一条“树叶鱼”;可以想起奶奶从别家挤来的羊奶温热好后的腥味,和院子里绊倒我的土坑。但我又想不起来那时几年几岁,想不起来被狗咬烂的伤口在哪,想不起来为何哭闹着不肯写字,硬是要跟着奶奶剥棉花。甚至想不起来,我有多久,没回过家。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不是我的家,那是一个个水泥盒子,来躲避自然界的风雨,当闪电雷声穿破云层,当马路上开出朵朵形色各异的雨伞,当气流咆哮着从我身边冲开,头发被卷得糊住眼睛时,我知道,我该躲进水泥盒子里。
林枫欲老柿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
自然界的坏天气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傲娇脾气,你看公园的彩虹,叶尖的水滴,穿着小雨鞋踩水上学的学生,就连阳光都带着新鲜的味道。这是雨过天晴。但心里的坏天气是阴暗的梅雨季,断断续续,凄凄冷冷,偶有的晴天会让人暂时忘记痛苦,但并不持续太久,因为这股潮湿还会再次侵袭,或许是在某个安静的夜晚,或许是在人声鼎沸的饭局,或许是在午后休憩醒来时分,我裹紧毛毯,四肢冰凉但眼泪滚烫,好奇怪,这水泥钢筋怎么无法御寒?电话线的那头是老人家慢悠悠的腔调:“今年咱家柿子树结了好多果儿,可大,卖了几百块钱呢!”
“……嗯。”我不敢多说什么,怕电流盖不住哭腔,惹得老人担心。
“你那里冷不冷啊?平常饭能吃好不?你们城里有暖气应该不冷……”
“今年过年还回来吗?”
……
清风拂故耳,秋叶落寒厅。
叶落归根是人类的一种执念,尽管我还未到叶该落的秋天,但仍然怀念我的根,那个无忧无虑的根。但当奶奶提着大包小包站在车站时,我才明白我怀念的不是那个承载童年回忆的小村,我是在思念那个陪伴我成长的人,那个带着自己做的辣酱和馒头,笑眯眯地问我吃饭了没的奶奶。原来这个出租房也可以这么温暖,奶奶坐在我的对面看我狼吞虎咽,昏黄的灯光和记忆里老屋子的灯泡重叠,空气里的潮湿似乎被它烘干,发霉的石头也会开出花苞,麦子蒸熟的香气是奶奶带给我的普鲁斯特效应,我在锅盖掀开的热气中鼓掌,我在烫手的温度里尖叫,我在重逢的喜悦中流泪,我在这个普通的日子里幸福。
我对于儿时的记忆总是清晰又模糊,模糊到我记不起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清晰到,我记得奶奶的爱,那是精描细写又暗喻隐藏在时光里的灵泽,滋润我,呵护我,成为我。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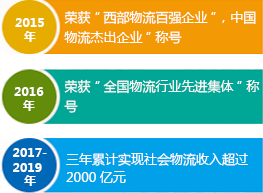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