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是小区院子里出了名的“疯猴子”。滑滑梯、健身器材上,哪哪儿都有她的身影。她爸说:“这点随我!我小时候在村里,也是带着全村同龄孩子上房揭瓦,想一圆自己的武侠梦。”所以,她毫不费力地把三条防蚊裤崩线开了裆,两只小袜子漏出脚丫子的大拇哥。其实,此乃常事。
夏日午后,乌云密布,风雨欲来。我看窗外的暗云涌动,便知滂沱的大雨将至。果不其然,顷刻间雨声哗哗响起,雨滴猛烈地跌落在窗台上。几分钟后,雨慢慢小了下来,隔着窗户只听见沙沙的雨声。我打开窗,清凉的风扑面而来,瞬间惬意无比,此时窗外的台阶上已积了浅浅的水,伴着细雨泛着小小的涟漪,树木在雨的洗涤下也焕然一新,变得愈发苍翠,几只鸟儿在草地上跳动着,一切都仿佛获得新生。这样的天气,舒适宜人,女儿的小脑瓜从空调被中露出来,正安稳睡着午觉。
这样难得的凉爽时间,没有不绝于耳“妈妈、妈妈”地叫喊声萦绕在耳边,突然拥有了片刻安静,应该做些什么能打发时间呢?目光触及椅背上搭着的衣物,得,有事干了,把丫头的裤子和小袜子缝补好。
我拿出一个铝制的饭盒,这是妈妈传给我的针线盒。饭盒的颜色早已发黄,表面还有一些磕碰的痕迹。记忆里,这饭盒是母亲以前上班时带饭的工具,配套的应该还有一个白色尼龙线钩织的网兜。那时下班后,母亲骑车去幼儿园接我,我坐在老式二八大杠自行车的横梁上,看着饭盒忽悠忽悠的晃着,一晃一晃,我就上小学了。后来听说铝制品长期使用对身体不好,就被新买的不锈钢饭盒替代了,铝饭盒被勤俭的妈妈洗刷干净当了针线盒用。再后来,我成了家,母亲说为人妻子,好歹要会点儿女红,没事儿订个扣子、补个袜子也是需要的,于是,这个针线盒就归了我。
我掀开盖子,从针线盒里翻找出同色的针线,倚靠在沙发上准备缝补,突觉室内光线有点暗,又不想开灯,于是拿个小板凳移坐到窗前,打开手机里的听书APP,就着窗外的亮色,一针一线,缝缝补补。
窗外的雨雾,美得迷离。柔风一缕,伴随着手机播放的富有情感的读书声,时间好似逃遁倒退,深印在母亲年轻的时候。
那会儿,物资匮乏,衣服裤子总是会买大一到两个号码,袖口和裤脚都是先挽起来缝住,长高了再放下来。小孩子贪玩也不爱惜衣服,我的裤子总会在两个膝盖处最先磨破。对我来说,母亲的针线活就像是一门艺术,缝出来的针脚总是疏密有致,走线笔直。就算是打补丁,也会神奇地缝出可爱的图案,就像是衣服上原本设计的一样。
我最爱倚着母亲看她缝补衣服,每次母亲都会借着窗外的阳光,低着头,满头青丝垂下,她用捏针的手将垂落额前的头发拢在耳后,恬静的模样在我眼里好似整个人都在发光。我总会赶紧拿本图画书,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一边假装看书一边偷瞄着母亲。母亲一边飞舞手中的针线加快缝补速度,一边说:“别离我太近,小心扎到你。”我扭捏着虚虚地将小板凳往外假装退一点,其实还是紧紧依偎着她。母亲无奈笑笑说:“你把你看的书大声念出来给我听,我会缝得更快哦。”于是,我赶紧坐挺身体,放声朗读起来,似乎在给母亲打气加油。很快,母亲将裤子缝好后收针并抖开。“试试吧,以后穿衣服要小心,再破了我就不管你了。”我心虚地吐一下舌头,穿好后去找邻居小伙伴炫耀母亲的手艺了。母亲言笑晏晏,笑容里透出一丝享受,看向我的目光更加柔和。
慢慢地长大了,我也会跟着母亲学点缝补技巧,甚至承包了她穿针的活计。一开始,是我主动的,再后来逐渐发现母亲的眼睛老花的厉害,还因为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也就只能指望我穿针了。往后的日子里,穿针由我代劳,而缝补的事宜,母亲仍乐在其中。
针线穿透布料,进进出出,在时光流逝中,母亲一件件把手中的针线活儿完成。而那个满头青丝的青年母亲象形,已经逐渐变化为眼角的皱纹和鬓边的白发。岁月,无声刻录着时光的流逝,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母亲用针线缝起了我贴身的暖意,更是缝补了我童年对美好的向往。
怔愣间,我突然觉得,这一切好似翻印在我和女儿身上。母亲对女儿的爱和心思都藏在那一针一线中,简单、纯粹、诚挚。
细雨依旧,微风轻诉流年,缝补间旧时光一去不复返,然款款永驻心间。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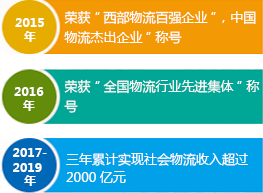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