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里的那一抹豆香,让房檐下挂着的冰凌在“滴答”声中消融,让阳光透过层叠的云层扑面明媚。推动时光的磨碾,四季更迭,步履匆忙。
忙碌推碾的,应该还有我记忆中的外公。
榆林的豆腐相当有名,也是日常及年节里必不可少的吃食。我小的时候,大概两年去一次远在榆林的外公家,每次都是赶着过年,那正是当地最冷的时候,风刮在脸上就跟小刀子划过一样。除了记得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外,那吸溜鼻涕的声音也一直萦绕在耳边。但这,依旧无法抵挡我对榆林的热爱,除了与亲戚邻居热闹地团聚,更让我难忘的是榆林的豆腐。
榆林豆腐质地紧实,味道独特,都说麻绳拴豆腐——提不起来,唯有这榆林的豆腐就能提起来,真是一绝!每次从外公家回来,都要想办法带点儿豆腐,那时候没有抽真空的设备,一般的操作是提一桶水,再将包好塑料袋的豆腐泡到水中保鲜,连桶带豆腐小心翼翼地坐大巴车提回家。
我除了爱吃,更爱看豆腐的制作步骤。只要外公说:“走,挑豆子去。”我一定第一时间从炕上跳下来冲到厨房,找一个大搪瓷碗和竹簸箕,一蹦一跳地跟着外公到窖房挑豆子。要想吃好豆腐,首先就要选好黄豆。我巴巴地看着外公解开布袋子封口的绳子,再一碗一碗地把豆子舀到竹簸箕里,抓起一把摊在手心,用右手铺平,一边挑一边给我教:“这种要不得,瘪了。”“这种也不好,你看,有小虫眼儿。”“像这种圆圆胖胖的就是要用的好豆子。”我歪着头看着外公专注的模样,也一下认真起来。心想:“妈妈说外公是省劳模,没想到连挑豆子都这么认真,我可不敢马虎呢。”
挑好的黄豆最起码得前一天的晚上就泡上。竹簸箕里的豆子“哗啦啦”的倒进一个铝制的大盆里,清洗的时候再把一些漂浮起来的“漏网之鱼”挑出去,就可以开始泡豆子了。一盆清水、一夜的浸泡,第二天,每一粒黄豆都涨得大大的、圆圆的,在盆子里“整装待发”。
等到中午暖和一点儿的时候,外公和舅舅一起将泡着豆子的大铝盆抬到石磨边。一个人舀水舀豆子,一个人推磨。看上去很有意思的活计,等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起先,我都是跃跃欲试要去推磨,每次的结果都是沦为给磨眼儿里舀豆子的那个。不到五圈,先不说筋疲力尽,肯定已经眼冒金星。伴随着隆隆的磨盘转动的声音,像牛奶一样的白色豆浆从磨盘嘴里流出,淡淡地豆香就弥漫在空气中。用大桶接好,再通过专用的滤布倒入另一个大桶里。滤布上过滤下来的豆渣还可以炒、可以和面粉和在一起或蒸或炸。
将装满豆浆的桶提至灶台旁,就可以开始烧火煮豆浆了。火候是关键,沸腾的豆浆表面冒着泡泡在不断翻滚,豆浆的香气溢满整个厨房,我早已迫不及待地拿着碗站在灶台边,碗里已经舀好了一勺绵白糖,只等着外公给我倒一勺豆浆喝喝。每次外公都又好气又好笑的说:“真是个饿死鬼托生。小心烫啊!”我则是小心翼翼地端着豆浆等降温,随着豆浆表面逐渐凝固一层薄薄的豆皮,我就溜着边开喝了。豆浆淳朴的香气弥漫在口腔,继而温暖了胃,温暖了整个身体,那股暖,嵌进了儿时记忆,那缕香刻进了岁月深处,历久弥香。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点豆腐了。榆林豆腐好吃,除了当地水质好,更是因为点豆腐不用石膏而用酸浆。酸浆是制作豆腐后沥出来的汁水,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以自身的乳酸菌发酵变酸。一般来说都是前一天的酸浆第二天使用,循环往复。有时候家里没有酸浆了,到邻居家借一碗就可以了。点豆腐也是个技术活儿,一般都是外公操作。装满酸浆的碗端的高高的,细细且均匀的落在豆浆锅里,随着大炒瓢的缓慢搅动,豆浆开始凝结出一朵朵浆花。酸浆滴落的速度和流量一定要控制好,不然肯定成功不了。当然,外公上手,没有不成的时候。慢慢的,豆浆凝固,此时要盖上锅盖再焖一会儿,等再揭开锅盖的时候,水豆腐就做成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豆腐脑,放上白糖或者提前调好的辣子醋水,就可以开吃了。
要真做出那种可以用麻绳提起来的豆腐,还有一道工序,就是压豆腐了。豆腐点的好,还要压的光。压豆腐的木质槽框大概长80公分,宽30公分,高22公分左右,槽板长宽各加10公分。将水豆腐倒在笼布中放在模具里,压上重物,水分就被挤压出来了,隔上三五分钟,再把笼布扎紧一点儿,不到半个小时,豆腐就做好了,从模具中倒出来,四角饱满,块形完整,表面上还印着笼布的肌理和模具的压纹。
“皮细膘灵”是外公做豆腐的终极要求,而我,则是嘴馋于豆腐后期深加工的美食。炸豆腐是我的最爱,豆腐切成薄片下油锅炸至金黄,切成三角形后与西红柿一起进锅烧煮,等炸豆腐吸饱西红柿的汁水后,再放入切好的韭菜段,出锅后,不但颜色漂亮,味道也是一绝。
时隔多年,外公离开我们好几年了,他把做豆腐的衣钵传给了舅舅。当然,现在早已用上了豆浆机,买豆腐也比以前方便很多。但是老家一直保留着年夜饭自己做豆腐的传统,就好像外公依然在我们身边一样。那份团聚,那份热闹,那份温暖,在滚动的石磨声和流逝的时光中,让豆香随着记忆氤氲蔓延,无声无息地温暖了整个岁月。
真想啊!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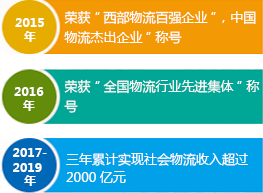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