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一个最简单、最普通的词汇,哪怕只是小学生,也懂得它的意思,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最神奇的词语,好像只要将它书写在纸上,在为它浇上清水,过一会,便能枝繁叶茂。于是,一个家的模样便跃然于白纸之上。
但是,白纸之上的,毕竟只是家的根,看的见,却触不到,稍微过上几天,在思念的长河中,便慢慢的枯萎,化成了满张的“念”字。对于旅居他乡,走南闯北的人儿,故乡这个词汇便成为了最浓的乡愁,在血液之中久久难以散开。
所以我们那的后生们,不管是升学、出工还是参军,当他们在离开这片滋养他们的土地时,都会带些家里的吃食,有挂面、油糕。而只有这样,哪怕鱼儿游的再远,也能寻见回家的路,就好像风筝飞的再高,那根牵连的绳子也总是在那里一般。所以,我们的“家”便随着走南闯北的人儿,飘散在了大江南北,逐渐化为了浓浓的,不会飘散的乡味。
那还是四十多年前,父亲年轻的时候,那也是他第一次离开故乡。那时太奶奶还在,在父亲外出的前夜,用糜子面给父亲蒸了一锅的黄馍馍,父亲嫌麻烦,不愿意带,太奶奶敲了敲父亲的头,说:“出了门,害了肚子,带点家乡的吃食,总是好事。”于是,父亲的行囊中,便多了满满一布袋的黄馍馍。但是那袋子黄馍馍却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火车上,父亲认识了同样是生长于黄土高坡的母亲,而认识的途径,便是那代表了身份的乡味。相互交谈下,来自隔壁县的两个人都是去往同样的一座城市,于是,乡味变成了两人的红绳,在一座远离故乡的火车上,牵起了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的心儿。
随着太奶奶去世,爷爷奶奶带着全家南迁,故乡离父母越来越远,尤其是在我出生后,父母回乡的机会更少。但随着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回家祭祖的使命便落在了身为长子的父亲身上。前年清明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一起回了一趟老家,坐在属于爷爷奶奶的窑前,端着满满的一碗羊肉饸饹,我突然有点了解爷爷奶奶有时拿着一张老照片端详半天的心情,那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凝聚着老人们永远无法割舍的乡情。
离去的时候,姑奶奶给我和父亲装了满满的一袋糜子面,奇怪的是,当我双手结过布袋后,却从中闻到了一丝爷爷家中的味道,但我确认,爷爷家并未有那里存放着糜子。于是,故乡和他方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里慢慢重合、混淆,最终在这浓浓的乡味中化为了一个“家”字,在笔直的大道上,留下一路温馨的芬芳。
一路的马不停蹄,带回来的糜子面,被爷爷奶奶蒸出了满满一锅黄馍馍,而当馍馍端上桌的那一刻,我分明看到爷爷奶奶眼中微微湿润,随后两人相视一笑。低下头后,那一颗游子的心,在浓重的乡味只剩落回了故乡的土地,踏实又安静。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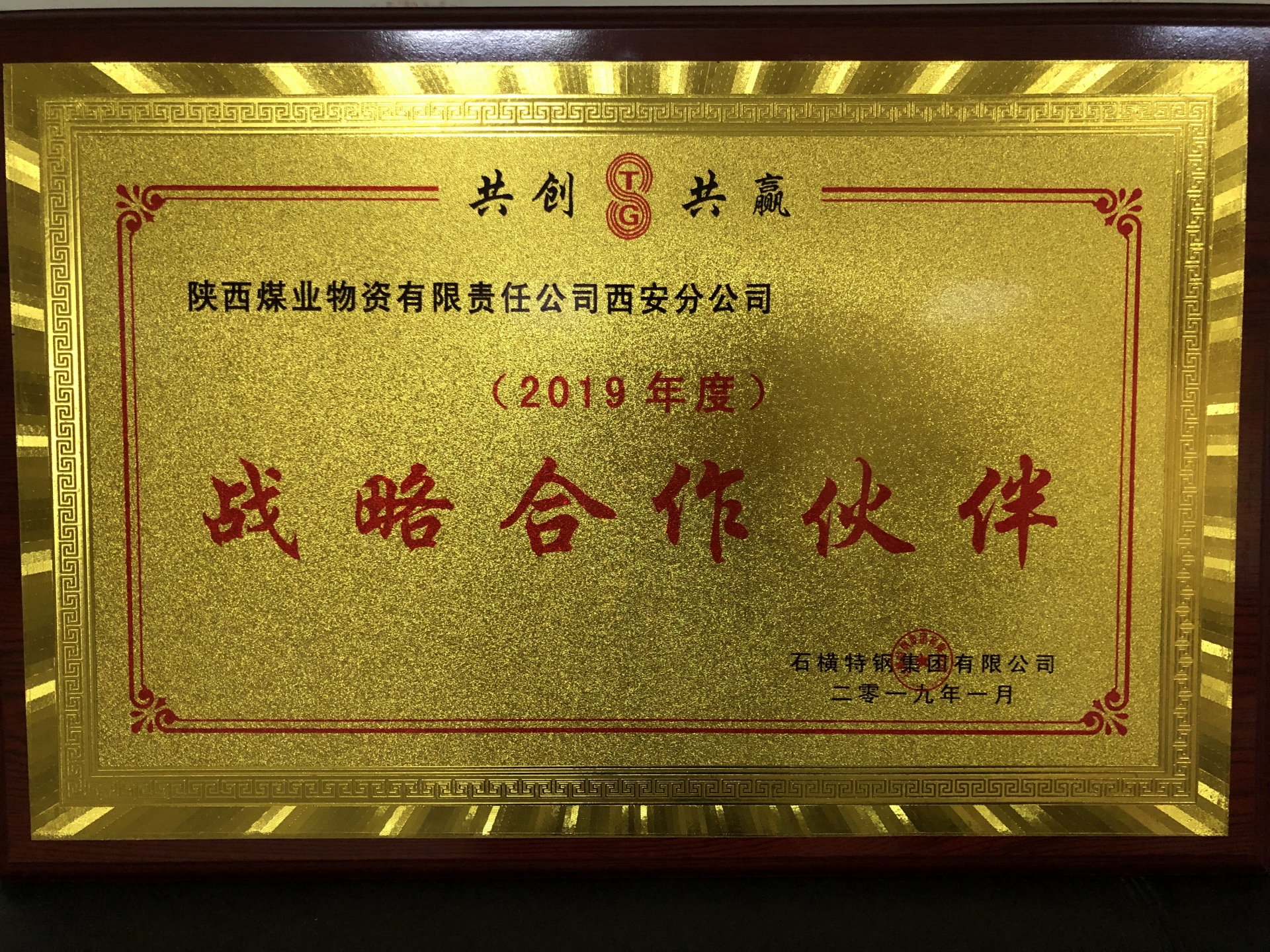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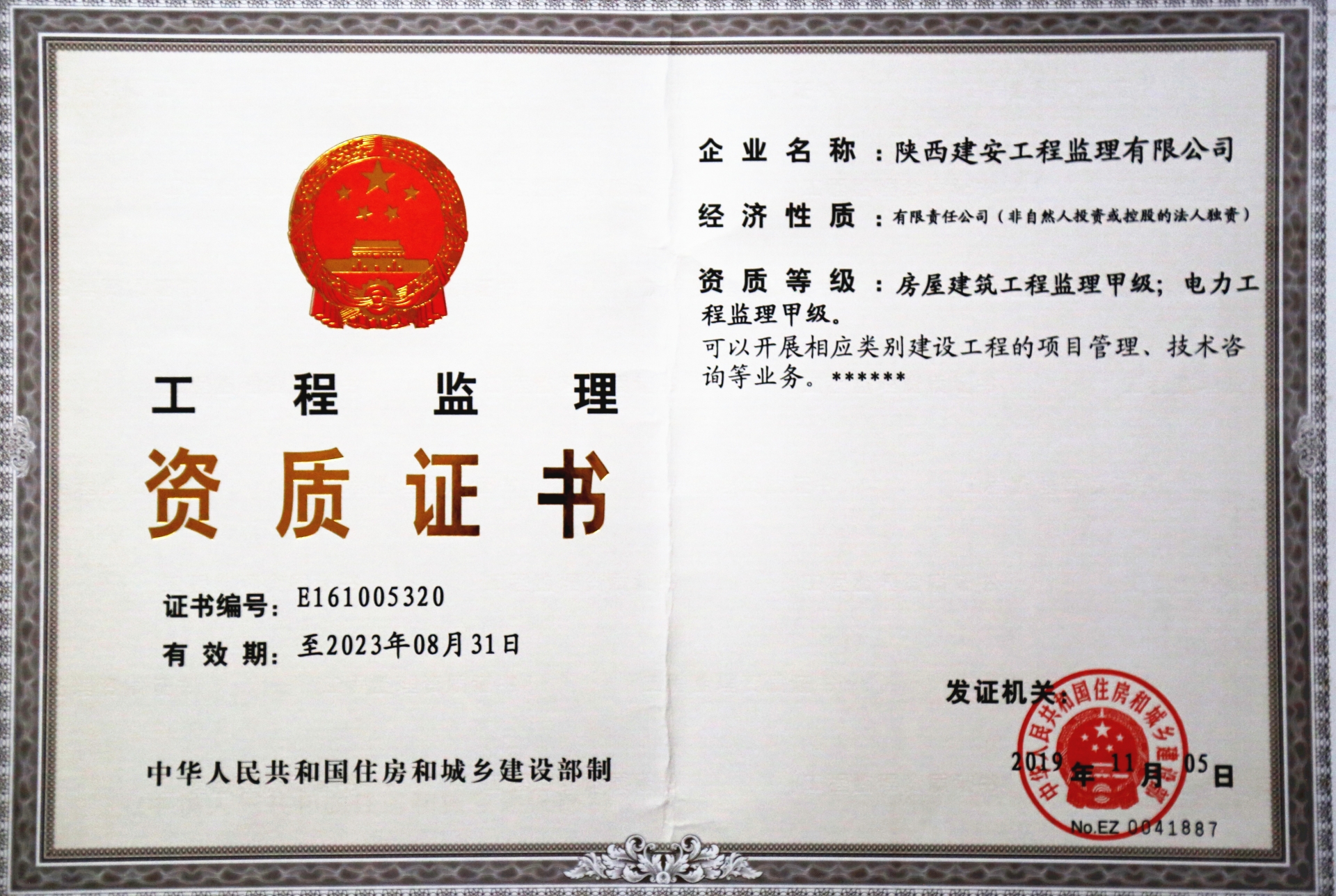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