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边城》的结尾处写道:“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虽然边城所写的是水乡的吴侬软语,却让我不禁想到了陕北慈爱宽厚的黄土地,来人世已久,也走过许多的地方,看过许多地方的人,听过许多种的曲子,我却偏爱我的故乡——陕北,那苍莽的高原,那热情豪爽的乡民,那高亢雄美的陕北民歌,都承载着我所有的偏爱和自豪。
陕北就像一坛苍莽而灼烈的酒,一口喝下去只觉得五脏六腑都溢满了热气。陕北舒缓起伏的塬如同安眠小调般,连绵起伏、纵横交错、形态各异的山峦交织着,如同一幅黄绿相间、层林浸染的战阵图,有人说,“七沟八梁一面坡,不是爬山就下沟”,连绵不绝、一层又一层的黄色梁峁,如同岁月和自然无情的奏响的琵琶,在一声声清冷和寒意中偏偏迸发着火热的战意,永不服输,坚韧而挺拔。
当你爬上山梁,看着眼前茫茫的一片山,苍苍莽莽,不见边际,你不禁生出一种磅礴的勇气和力量,耳边呼啸的风仿佛是匈奴金戈铁骑的响踏声,你能感受到红军行进在这群山之中时坚定地信仰,如豹子在捕猎前绷紧肌肉的那一秒的蓄势待发,一种磅礴的气势直冲云霄,似乎只要踏在这片黄土地上,你便能一往无前,世上再无难事可阻。
陕北的人耿直憨厚、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就像我们喜欢吃的辣椒,也叫辣子,热辣辣的,真性情,不耍滑头,也没有花花肠子,就像一碗油泼辣子面,看着火辣辣的,吃下去也是火辣辣的顶到胃里,然后舒舒服服服的出一场汗,神清气爽;陕北女人很温婉秀丽,柔中带刚,敢爱敢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写了陕北,孙少平和孙少安都是典型的陕北汉子,坚韧而乐观,无论是挖煤赶山路的辛苦,还是出意外后毁容的面孔,都没有磨灭他们对生活的热情。陕北的水也是好的,有人叫陕北的水叫“桃花水”,意思是女人吃了那水能面如桃花。“闭月羞花”的貂婵,就是陕北榆林米脂人,就是吃着那水长大的。
陕北的吃食是令人难忘的,就像牵着风筝的线,风筝走得再远飞的再高也还是会有一条被牵着的线,“民以食为天”,故乡的吃食就像一把小钩子,提起故乡,总会顺带着勾起味蕾,接着馋虫滴溜溜的上了脑,脑子里想的全是陕北的吃食,什么洋芋擦擦啦,馃馅啦,油旋啦、马蹄酥啦,羊杂碎啦,凉面等等......别的地方是再难吃到这正宗的味道的。
陕北的四季也是与别处不同的。陕北的春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也不是“润物细无声”,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春天那般娇滴滴的像个小姑娘,陕北的春是从漫长的寒冷和狂风中慢慢地,一步步走出来的;然后夏天就像个小子,咯噔噔的跑来,人们接着从毛衣长褂中换到短裤体恤,爽利利的毫不拖沓;秋天就像染着红色和黄色的盘子打翻了,与土地融为一体,发着热热的气;到了冬天,便是漫长的寒冷,但我喜欢陕北的冬天,陕北的冬天是冷的,更是热闹的,敲锣打鼓的,红绸子舞来舞去的秧歌,家家户户的烟火气,塞满着陕北的冬天。
陕北的雪也是大气的,陕北的雪若是下,便是痛痛快快的下,不会小家子气气的下一点,若有若无,好像没有味道似的。陕北的雪漫漫的下来,盖住辽远的土地,大雪纷飞之初,白雪黄土相间,山川萦绕好似梨花随风漫散。
陕北是开放而包容的,陕北没有根深蒂固的、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陕北能够以它博大的胸襟接收和包容外来民族和外来文明,并且为之提供了融合新生的空间和土壤,所以陕北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在党的惠民政策的影响下,乘西部大开发的东方,依靠特有的自然资源,奋力拼搏,改天换地,经济一日千里,飞速发展。
我爱我的故乡陕北,我的魂在陕北,无论我走到哪里,飞得多高,我的心永远为陕北而满腔热忱,无论我行到何处,念一声陕北,心中便激起千尺浪花。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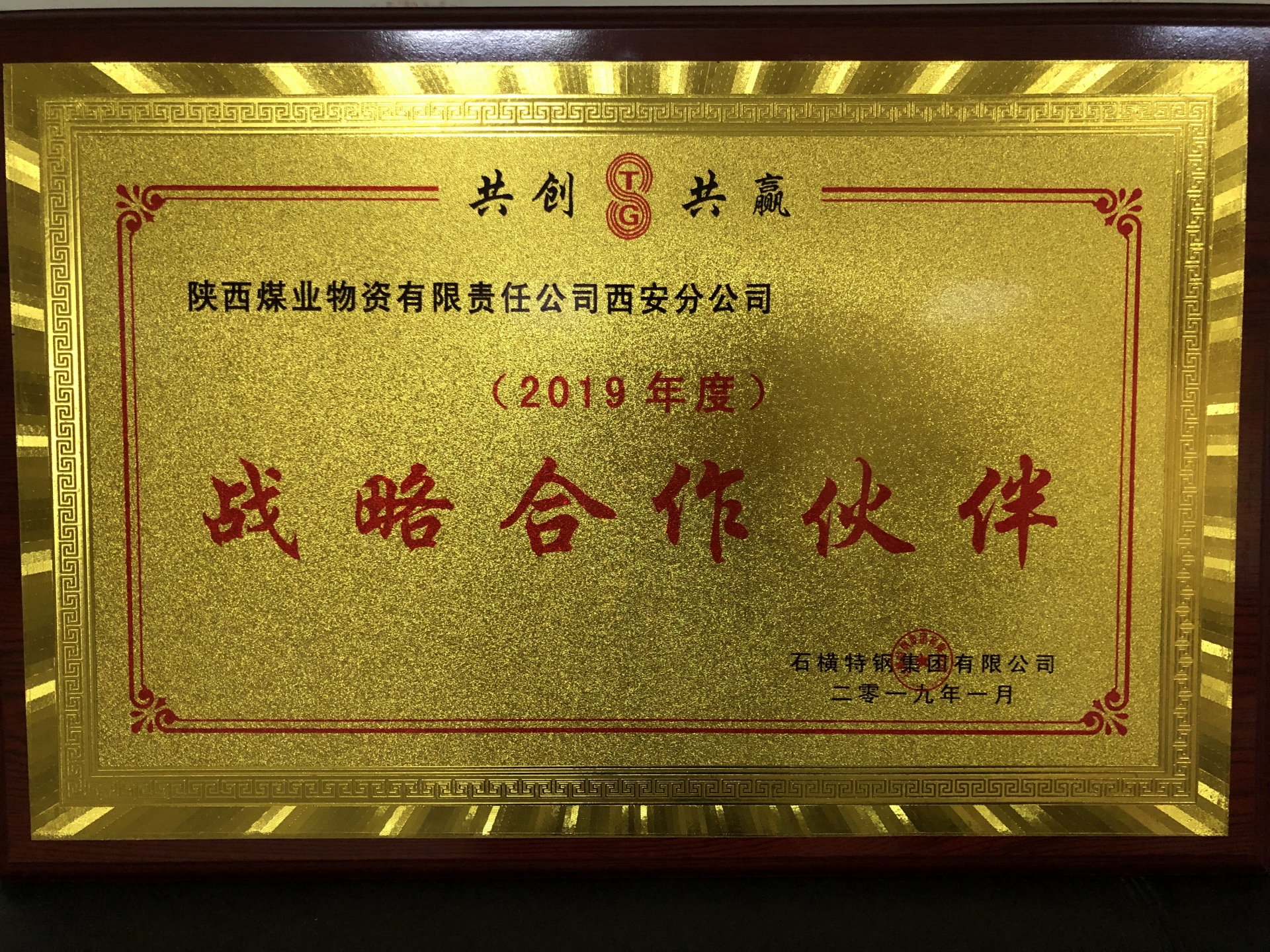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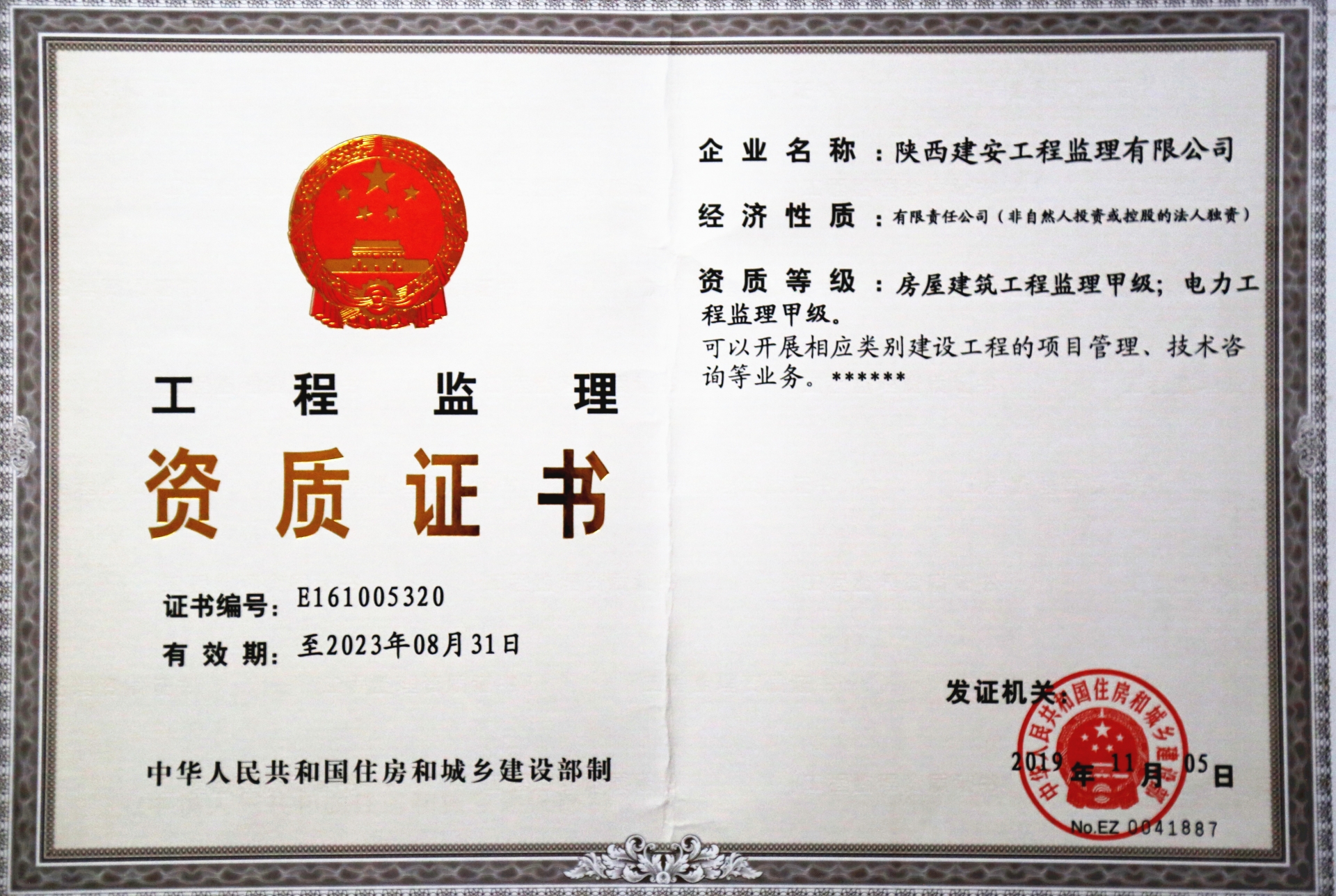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