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窗口的阳光,针线筐里的针插和彩线相应成趣。在时光的一针一线、一缝一合中,成就了姥姥、妈妈、我,三代人针线传承的故事。
姥姥姓吴,生于建国前,她没有大名,裹着小脚、也不识字,是在嫁给有文化的姥爷之后,姥爷才给姥姥取了大名。在我的印象中,姥姥总是摇晃着身体。妈妈说那是因为裹脚太小无法长时间的停留站立,只能不停来回前后左右地踱步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姥姥一生养育了五个子女,由于姥爷是省劳模,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姥姥用自己瘦弱娇小身体一肩挑起。
妈妈经常对我说:“我小时候全家人都穿着姥姥做的鞋和纳的鞋垫,那时候大多数人家都是穿自己做的鞋和鞋垫,但能做到像你姥姥这样针脚细密、花样繁多的却不多。回想起来满满都是温暖而骄傲的记忆。”妈妈还说,她小的时候,穿的衣服也是姥姥手缝的,经常是将姐姐的衣服改小给妹妹,浅色的衣服染深色变着花样穿。而在我的记忆中,姥姥确实特别爱做鞋垫,我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厚叠她做的鞋垫,因为太喜欢这种手工的鞋垫,觉得跟工艺品一样,根本舍不得用。其实我们这些孙辈的孩子们都不让她再做鞋垫了,怕伤眼睛,而她觉得这是她能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每次回姥姥家,我都能看见姥姥忙里忙外之余,坐在炕桌边做鞋垫,家里的碎布头都成为她眼里的宝贝,洗好晾干,收拢在一起。记得小时候,姥姥家有一个绛红色的包袱皮儿,里面包着的一堆碎布头。每当她拿出来,我们这些小辈儿都像挑宝贝一样在里面翻找自己喜欢颜色的布头,然后拿起针线学着姥姥的样子胡乱缝起来。玩够了,扔在一旁的布头会被姥姥小心的拆好,再整整齐齐叠在一起,码好放在包袱里。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姥姥靠双手一针一线养大了五个子女。
妈妈是建国之初出生的,她是家里的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企业,退休时是她们办公室里唯一的女高工。妈妈虽然没有接续姥姥做鞋垫的传统,但她也有一双巧手,住在单身宿舍时,跟舍友一起绣桌布。小时候,那块桌布一直搭在我家的餐桌上,精美立体的绣花让我一直以为那是买来的机绣成品,当妈妈告诉我那是她亲手绣的时候,让我简直惊讶的合不拢嘴。
我小时候,爸爸还在部队工作,妈妈作为职业女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承包了我的快乐童年。我上小学以后,上下学提书的布袋子就是她用缝纫机给我做的,同学们见了喜欢,妈妈还做了好多分送给她们。那时候结婚都流行“三转一响”(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收音机),而我父母结婚时经济拮据,什么都没有买,家里那台老式的缝纫机是我上小学以后爸爸才给妈妈补买的。那时家里条件一般,我很羡慕小伙伴的洋娃娃,妈妈说如果期末成绩好了,就给我做一个布娃娃。我每天认真做作业,预习复习,满脑子都期待赶紧到期末考试,一定考出个好成绩让妈妈给我做布娃娃。记得那个学期末,我考了全班第二,发成绩的当晚,我是在妈妈“哒哒哒”的缝纫机声中睡着的。第二天醒来,枕边放着一个50公分长的布娃娃,穿着妈妈给我做裙子剩下布料的同款小花裙,带着有花边儿的帽子,太美了,我兴奋得在床上跳来跳去。妈妈凭借着那台缝纫机,让我的童年在踏板声和转轮的转动里快乐成长。
而我,算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刚好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父母应晚婚晚育的政策30岁才生了我。耳濡目染吧,我从小就喜欢手工,小时候流行一种折叠剪刀,是我书包里的必备,没事了掏出来剪个纸片也让我很快乐。
后来,我上大学学习了跟美术相关的设计专业,这让我的手工能力得到了更大的提升。不论是十字绣、刺绣,还是拼布、钩针抑或是扎染,我都愿意学习尝试。婚后,我也拥有了自己的电动缝纫机,再也不用像妈妈那样手脚配合着踩缝纫机了,只要插上电源,右脚轻轻搭上踏板,电动缝纫机就“哒哒哒”的开始运行了。有了这台缝纫机,让我DIY改造旧衣服的爱好得到了“长足进步”,用老公和自己不穿的旧衣服,给我的女儿从出生之初做了小鞋子、小帽子,到如今做了上幼儿园的小书包、做了参加活动穿得汉服,让她经常在幼儿园一脸骄傲地转着裙子说“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而最让我得意的作品是用女儿的胎发和碎布头制作的胎发画,特别有纪念意义。还有跟着母亲学做的盘扣,这可是姥姥祖传的手艺,如今盘扣用的地方少了,我就把盘扣改造成了耳环。当盘扣耳环在颈肩的流转跳跃时,让我们三代人的巧手与时代接轨,恍惚间听到了姥姥和妈妈的指尖絮语。
当然我的“巧手”也在工作中也开始“大展拳脚”,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书画比赛,各种活动投送的剪纸作品、漫画作品也经常登场。之前还为陕西省纪委创办的微信公众号“廉水谷”的每日推文配画过廉政插画。当我把爱好和工作紧密结合之后,我觉得工作的幸福感更高了。
今年是祖国成立的70周年,从姥姥把手缝针当作养家糊口的手段,到妈妈的老式缝纫机成为成节俭持家的法宝,再到如今我的电动缝纫机成就了我生活的小乐趣,甚至是创意的不断延伸。时代的改变是从生活中的细节体现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但指尖的传承将不断延续,见证着新中国的七十年的经济变化和发展伟业。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集团概况
集团概况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企业板块
企业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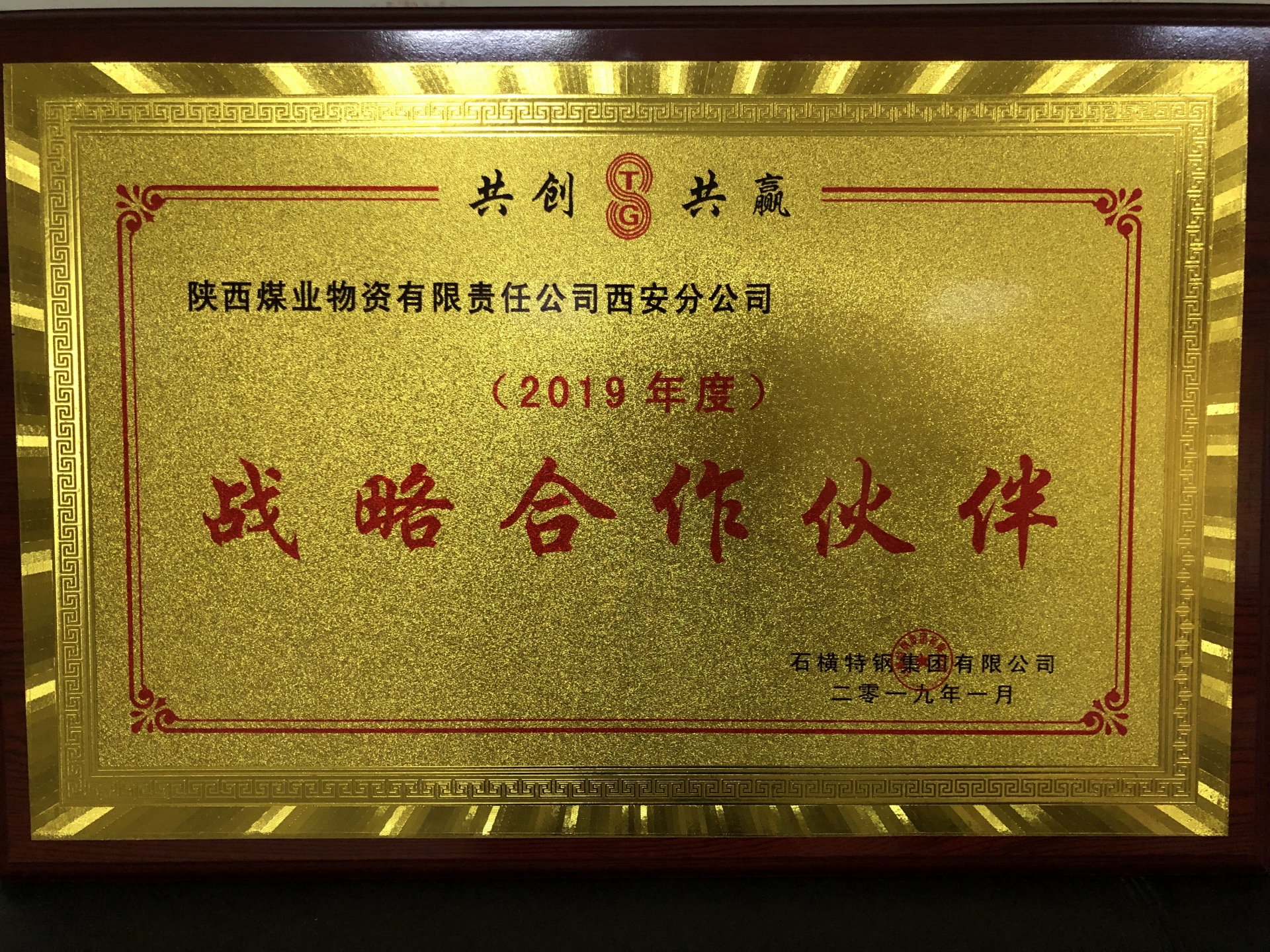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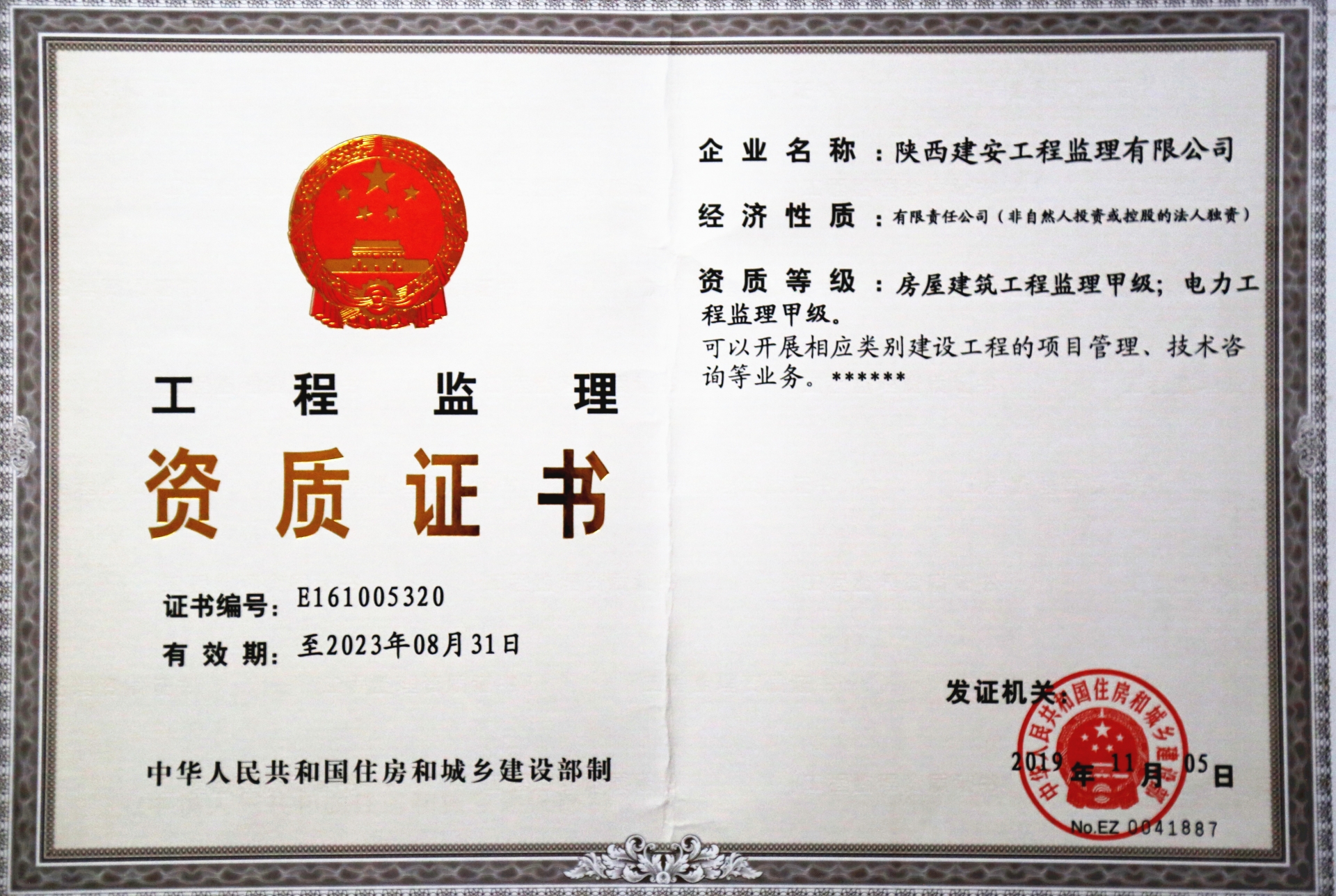


 物资服务
物资服务 陕煤物资商城
陕煤物资商城
 西煤云仓
西煤云仓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供应商协同管理平台
 招采平台
招采平台
 主数据
主数据
 内部大市场
内部大市场
 商务智能
商务智能
 办公系统
办公系统 OA系统
OA系统
 邮箱
邮箱
 党费缴纳
党费缴纳
 VPN
VPN
 企廉网
企廉网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